|
天光未亮,周家三兄弟已经起身。 周良洛推开柴房的木门,冷风灌进来,带着深秋清晨特有的凛冽。他回头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大哥和三弟,轻手轻脚地走到院中,从井里打上半桶水,就着冰凉刺骨的井水洗了把脸。 冷水激在脸上,睡意彻底消散。他抬起头,看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,深深吸了一口气。 今天是他们三兄弟独立门户的第一天。 三个月前,父亲在采药时失足坠崖,重伤不治。母亲本就体弱,接连半个月不吃不喝,硬撑着办完父亲的丧事,在一个雨夜也撒手人寰。短短一月之间,周家三兄弟失去了双亲,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。 “二弟,起这么早?” 周良茂从屋里走出来,手里攥着一块粗布帕子递给他。大哥今年十九,比周良洛大两岁,生得高大结实,面容憨厚,眉心却总拧着一股化不开的愁绪。 “大哥,我想好了,今日就去镇上找活计。”周良洛擦干脸上的水,转身看向兄长,“你在家照顾三弟,我总能找到些事做。” 周良茂摇头:“不行,你才十七,去镇上谁肯要你?我去。” “大哥力气大,留在家里开荒种地才是正理。”周良洛的语气不容置疑,“我会写字算账,去镇上更容易找到活计。咱们三兄弟,各有所长,就该各尽其用。” 屋内传来窸窣声响,最小的周岸洛揉着眼睛走出来。他今年才十二,瘦得像根竹竿,脸上还带着未褪的稚气。 “二哥,我也去。” “你去什么去?”周良洛走过去,把弟弟的衣领整好,“你在家好好念书,日后若能考取功名,爹娘在天之灵也能安息。” 周岸洛低下头,眼眶红了。 这三个月来,三弟夜里常偷偷哭,周良洛都听见了,却从未说破。他们失去的不只是爹娘,还有曾经安稳的生活。但日子总要过下去,他是家中次子,必须撑起该撑的那片天。 天色渐亮,周良洛揣着大哥塞给他的三个杂粮饼子,踏上了去镇上的路。 周家村离清河镇有二十里山路,周良洛走得很快,他要赶在镇上铺子开门前到那里。山路崎岖,他却觉得每一步都走得踏实——有事可做,有路可走,就是希望。 到了镇上,周良洛先去了最大的杂货铺。掌柜的上下打量他一番,问了几句,摇了摇头:“后生,你年纪太小,我这店里需要的是能扛货的伙计。” 他又去了粮店、布庄、茶馆,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。要么嫌他年纪小,要么问他有没有保人——他哪来的保人? 日头西斜,周良洛坐在镇口的老槐树下,啃着已经凉透的饼子。 饼子很硬,硌牙,他嚼得很慢。累了一天,腿像灌了铅,但他想的不是自己,而是回去如何跟大哥和三弟交代。 “小兄弟。” 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。周良洛抬头,见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站在面前,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衫,手里拎着一个药篓。 “你是周家村的?”老者问,“我看你在这坐了一下午了。” 周良洛站起身,点点头。 “我在找一个人。”老者说,“会写字,认药材,人老实。工钱不多,管一顿饭。干不干?” 周良洛愣住了。 “我姓陈,在镇东开了一间小药铺。”老者笑了笑,“本来想找个年纪大些的,但年纪大的都嫌我这铺子小,不愿来。我看你在这坐了一下午,不焦不躁,倒是个沉得住气的。” 周良洛深深作了一揖:“陈老先生,我愿意。” 陈记药铺很小,只有一间门面,柜台后是一排药柜,散发着浓郁的草药气息。陈老先生的儿子从军多年未归,老伴也去了,一个人守着这间铺子,勉强糊口。 “我这里活不多,就是晒药、切药、抓药。”陈老先生点起油灯,对周良洛说,“你每日巳时来,酉时回,中午管一顿饭。工钱嘛,一月二百文。” 二百文,够买三十斤粗粮,够三兄弟吃半个月。 周良洛再次作揖:“多谢陈老先生。” “不必谢我。”陈老先生看着他,“我看你眉宇间有股倔强劲儿,是个能吃苦的。年轻人,肯吃苦,就有出路。” 回村的路上,天已经黑了。周良洛走得很快,心里却比来时亮堂许多。 走到半路,远远看见两个黑影。走近了,才发现是大哥背着三弟,正沿着山路走来。 “大哥!三弟!” 周岸洛从大哥背上跳下来,扑进他怀里:“二哥,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?我和大哥担心你!” 周良茂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:“找到活计没有?找不到没关系,咱们再想办法。” “找到了。”周良洛说,“在镇上的药铺,一月二百文,管一顿饭。” 周良茂愣了一下,随即咧嘴笑了,笑得很憨,眼眶却有些发红:“好,好,走,回家说。” 月光下,三个身影并肩而行,走向山坳里那间点着微弱灯火的土屋。 那夜,周良洛躺在床上,听着大哥和三弟均匀的呼吸声,久久无法入眠。他想起了父亲生前常说的话:人活一世,不怕穷,就怕没志气。 他闭上眼睛,在心里默默发誓:爹,娘,你们放心,我一定会撑起这个家,让大哥和三弟过上好日子。 窗外,月光如水。 山村的夜很静,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周良洛听着那有力的跳动声,知道自己的路,才刚刚开始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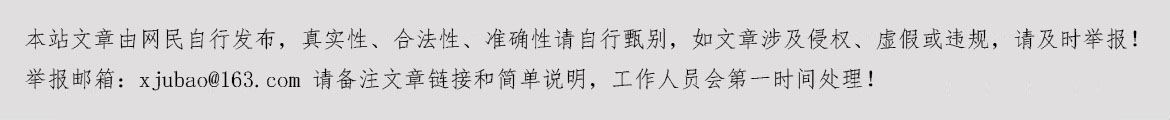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• 新闻资讯
• 活动频道
更多




